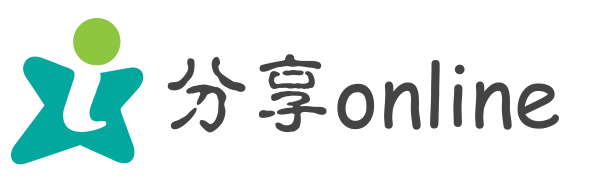粵夜煙火里,安徽姑娘的炒粉人生
夜幕低垂,廣東東莞的城中村街頭亮起串串暖黃路燈,油煙混著米粉的香氣在晚風里彌漫。晴子的炒粉攤就支在巷口最熱鬧的拐角,鐵皮推車擦得锃亮,煤氣灶上的鐵鍋泛著油光,她系著洗得發白的圍裙,正手腕翻飛地顛著勺,火苗 “騰” 地竄起,映亮她帶著汗珠的臉頰。這個來自安徽農村的姑娘,已經在這片異鄉的煙火里,用一把鐵鍋、一把米粉,重復了一千多個日夜。
晴子的老家在皖北農村,村口的老槐樹和田埂上的野草,是她童年最深刻的記憶。20 歲那年,為了給家里減輕負擔,也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,她背著簡單的行囊,坐上了南下廣東的綠皮火車。初到東莞時,工廠流水線的機械重復讓她迷茫,服務員的工作又總覺得少了點歸屬感。一次深夜下班,她在街頭吃了一碗熱氣騰騰的炒粉,那口帶著鍋氣的鮮香突然擊中了她 ——“我奶奶也會炒粉,不如我自己擺攤試試?”


這個念頭一旦生根,就瘋長起來。晴子拿出所有積蓄,買了二手推車、鐵鍋和調料,又特意找街頭炒粉老師傅請教。起初練顛勺,她的手腕酸得抬不起來,炒出的米粉要么糊鍋要么沒入味,一天下來營業額不足百元。有顧客吐槽 “味道一般”,也有人勸她 “姑娘家擺地攤太辛苦,找個安穩工作多好”,但晴子沒放棄。每天收攤后,她就在出租屋里反復練習,調整火候、琢磨醬料比例,土豆絲切得粗細不均,就練到手指發麻;米粉炒得粘連,就記下不同水溫泡發的時間。
如今的晴子,早已是炒粉攤的 “老把式”。每天凌晨四點,天還沒亮,她就騎著電動車去菜市場進貨。米粉要選本地的陳米制作的,筋道不易斷;青菜得挑帶著露水的油麥菜,脆嫩爽口;豬肉要選前腿肉,肥瘦相間才夠香。回到出租屋,她開始切菜備料,土豆絲切得均勻如絲,蔥花、蒜末分盒裝好,秘制醬料要按比例混合攪拌,這一切都要在中午前完成,才能趕上下午五點的出攤時間。
傍晚時分,巷子里的人流漸漸密集,晴子的炒粉攤前開始排起長隊。“老板,加蛋加火腿!”“少鹽少油,謝謝!” 顧客的要求此起彼伏,晴子都一一應著,手上的動作卻絲毫不停。倒油、下蒜姜爆香、放入肉絲翻炒至變色,再加入米粉快速顛勺,鐵鏟與鐵鍋碰撞發出 “叮叮當當” 的聲響,像是一首專屬的煙火交響曲。火候是炒粉的靈魂,晴子總能精準把控,既讓米粉吸足醬汁,又保持著根根分明的口感,最后撒上蔥花、淋上一勺秘制辣醬,一碗香氣撲鼻的炒粉就遞到了顧客手中。


擺攤的日子,辛苦是常態。夏天的廣東悶熱難耐,灶臺的高溫烤得她汗流浹背,一天下來,衣服能擰出半盆水;冬天的晚風刺骨,她的手凍得通紅,卻依然要保持穩定的顛勺動作。遇到下雨天,她得撐起大大的雨棚,小心翼翼地護著灶臺,生怕雨水澆滅爐火;偶爾遇到城管巡查,她又要推著沉重的推車快速轉移,氣喘吁吁卻不敢有絲毫抱怨。
最難熬的是深夜收攤后,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狹小的出租屋,卸下一身油煙味,手指上的繭子被熱水泡得發脹。這時她會撥通家里的視頻電話,對著屏幕里的父母強裝笑臉,說著 “我一切都好”,掛了電話,思念就像潮水般涌來。她想念媽媽做的紅燒肉,想念爸爸在田埂上的吆喝,想念老家夜晚的寂靜星空,與眼前這座城市的喧囂形成鮮明對比。但每次委屈想哭時,她都會摸摸手上的繭子,想起當初來廣東的初衷 ——“沒有富貴的命,就靠自己打拼”,這句話被她寫在手機備忘錄里,成了支撐她走下去的信念。
晴子的炒粉攤,漸漸成了巷子里的 “網紅打卡點”。附近工廠的工人、上學的學生、下班的白領,都成了她的老顧客。有人喜歡她炒粉的鍋氣,有人佩服她的堅韌,還有人會在吃粉時和她嘮幾句家常。有個經常來的打工小哥說:“晴姐的炒粉,吃著有家的味道。” 這句話讓晴子紅了眼眶,她知道,自己炒的不只是米粉,更是漂泊者對溫暖的期盼。


如今的晴子,已經攢下了一筆小錢,她計劃著明年租一個小門面,把炒粉攤升級成小店,再把老家的手藝加進去,推出安徽特色炒面、酸辣粉。她說:“廣東包容了我,我也想在這里扎根。” 每天重復的炒粉動作,在別人看來或許枯燥,但在晴子眼里,每一次顛勺都是對生活的熱愛,每一碗炒粉都是對未來的期許。
夜色漸深,街頭的人流慢慢散去,晴子開始收拾攤位。鐵皮推車的輪子碾過石板路,發出 “咕嚕咕嚕” 的聲響,與遠處的車鳴聲交織在一起。她抬頭望了望天空,月亮掛在高樓之間,溫柔的月光灑在她身上。這個來自安徽農村的姑娘,沒有驚天動地的夢想,只是憑著一雙勤勞的手,在異鄉的煙火里,書寫著屬于自己的奮斗故事。她的炒粉,炒出了生活的滋味,也炒出了平凡人生里最動人的力量 —— 所謂歲月靜好,不過是有人在煙火里默默堅持;所謂生活可期,不過是靠自己的雙手,把日子過得熱氣騰騰。